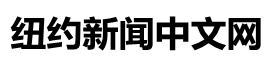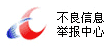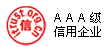本篇文章4855字,读完约12分钟
原文:王晶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王晶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历史 王,1986年至1995年任香港大学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特聘教授。曾在多个国家任教,在东南亚史和南洋中国史研究领域享誉海内外。 王1930年出生于荷兰殖民统治下的泗水,现为印尼第二大城市,距家乡江苏近2000公里。在随后的十年里,王氏家族几次试图回国都没有成功,最终定居在英国统治下的怡保,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 王晚年写回忆录时写道:我早年等待回国,最后又回到马来西亚的经历,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但也正是这个转折点,让他走上了留学海外的道路,成为了主要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 王庚武 这些都需要从王父母的移民经历来探讨。 王的父亲通常不谈论他的家谱,也不提及他年轻时的过去。关于他父亲和他祖先的故事,王大多是从他母亲这些年的经历中拼凑出来的,像一幅拼图,用的是历史学家细腻的笔触。 王的父亲米文,1903年生于江苏泰州。1911年,父亲八岁,和爷爷奶奶在武昌目睹起义。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王氏一家逃出武昌,回到台州。但是,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我爷爷王运城也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他不擅长做生意,是在朋友的推荐下进入银行的,但事业并没有什么起色。 好在儿子没有步父亲的后尘。从小到大,王米文在家里最崇拜的就是他的叔公王宗彦。当时王宗炎是著名的儒生,而王业山是叔祖的儿子,在武昌办学。王米文师承叔侄,在武昌系统学习经学、颜体书法、古诗。然而,12岁以后,王米文开始涉猎西学。他在台州进了一所新学校,专攻英语和数学,甚至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那里教了一段时间书。 王米文真正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可以追溯到他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学校始建于清末,数次更名,成为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台大的前身。当时的郭炳文校长深受美国教育哲学的影响,师从杜威(1859-1952)和保罗&米德多;保罗·门罗(1869 & ndash1947年).由于郭的努力,杜威和门罗在国立中央大学做了几个月的讲座,使这所大学一时成名。郭还邀请陶行知担任教育学院院长,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王的父亲选择了英国文学与教育。毕业后,王米文继承了母校开放免费的教育理念,在东南亚华侨教育中实践。1929年,王米文出任印尼爪哇岛泗水华侨高中校长,这是当地第一所华人高中。 当王米文在东南亚的事业步入正轨后,泰州的父母开始为他物色结婚对象。王家当时并不富裕。其实一家之主王运城失业了,家里开始依靠王米文的海外工资来帮助他。谁家女儿愿意去了门后马上去东南亚,开始一段完全陌生的人生旅程?当时,王的父母看中了附近东台镇的丁姑娘。 丁甲出生于镇江,公务员家庭,祖上在盐局工作。19世纪中叶,太平军逼近镇江,丁家逃往东台。虽然丁家的领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继承他们父亲的事业并获得名声,但20世纪初结束的科举制度迫使一些丁家的后代寻找另一种谋生的方式。在过去,盐役的人脉和经验得到了一定的利用,丁的生意对他们在东台的立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清朝覆灭后,他们原本的人脉瞬间崩塌。擅长儒家经典无助于改善商业。一些家庭的男人纷纷染上大烟,丁家开始分崩离析。 从小目睹家庭由盛转衰的丁,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但也很务实。她生于1905年,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丁出生时,丁家并未衰败,诗书礼仪、棋艺书法是丁女儿的必修课。她擅长小楷,喜欢看通俗小说,甚至包括父母不许接触的《红楼梦》。在丁看来,如果一个男孩从小就热衷于学习,而且很聪明,那么求知无妨。但如果资质平平,父母和家人也应该支持他们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以便将来在社会上立足。这种务实的性格也体现在她后来对儿子人生选择的支持上。 1929年,辛亥革命爆发18年,五四运动10年。新文化运动的风还没有过去。江苏附近的上海成为当时亚洲最多元化的城市,女性从着装到生活伴侣选择都在经历着各种变化。但是在东台和台州,大部分婚姻还是按照父母的命令和媒人的话来的。多年以后,丁在的日记里用小写写道:我于1929年2月结婚,直到婚礼,我们都没有蒙面。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彼此都有很好的好感,互相照顾,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几十年同甘共苦。 婚后不久,王敏文和新婚妻子踏上了泗水之旅。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股市全面崩盘。大萧条像瘟疫一样开始在全球蔓延,各国经济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经济衰退的冲击。西方对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的需求直线下降,以出口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南阳国家成为国际贸易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大量在种植园工作的中印苦力被遣送回国。 泗水古镇 王出生的时候,全世界都陷入了经济萧条。父亲工作过的泗水华侨高中,艰难地维持着,但由于创办学校的资金基本上来自当地华商,经营越来越困难。王米文和妻子奋斗了一年多。最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决定接受怡保中文学校的聘书,担任助理主管。在当时的王米文看来,英国统治下的马来联邦是他们回归中国的中转站。带着这个希望,一家人出发了。 对于刚来的王家人来说,30年代初的怡保确实给了他们一种回家的感觉。当地经济以采矿业为主。20世纪10年代,一场大火将一宝老街夷为平地。在殖民政府的号召下,当地的中国矿工开始更多地参与房屋重建和其他市政建设。20世纪20年代采矿业的快速发展使当地中国人受益。虽然1930年的大萧条对当地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在当时,华人商店是市民生活的主要部分,当地华人学校的基本运营得以维持。 从1931年到1941年,王氏一家住在怡保的绿城,离附近的新城不远。新城四面环河,交通便利,华人店铺众多,教育医疗条件发达。除了政府资助的安德森中小学外,当地天主教寺院、中英女校、育才中学、霹雳女校等都是以中文授课,分男女校,以马来语为授课语言的学校都位于附近的磅邦,这是一个讲马来语的村庄。相比之下,绿城安静得多,居民主要是非欧洲人,大部分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 当时王氏一家既觉得亲切,又觉得不舒服。原因之一在于语言障碍。 怡保的华商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大多讲闽南语、客家话和粤语。王米雯和丁祖籍都在北方。北方方言和普通话差别不大,但和南方方言差别很大。幸运的是,就王米文的工作性质而言,学校的班级、课本、老师都可以用普通话交流。丁兰佩在当地女佣艾伦的帮助下学会了一些粤语,以方便日常交流。 怡保(Ipoh) 也许语言习得是区分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经历的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就王米雯和丁而言,他们的母语无疑只有普通话和家乡话。除此之外,王米文也精通英语。然而,年轻的王却不是这样,他当时生活在南阳,南阳可能是世界上文化和语言最多样化的地区之一,也是自然习得多种语言的最佳环境之一。 在当时的绿城和新城,王的生活环境充满了丫鬟艾伦说的粤语,父母说的普通话和江苏话,客人说的上海话,商店里的客家话和闽南话,街道上的本地马来语,寺庙里的孟加拉语、旁遮普语和古吉拉特语,邻居的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殖民政府大力推广的英语。 从五岁起,王就开始在两种语言之间穿梭。一开始我妈希望他能像大部分当地的中国孩子一样进入当地的中文学校,怕他回国不久,中文水平跟不上。但是他的父亲接受了中西教育,说服他的母亲把他送到他家附近的麦克斯韦小学。同时,父亲开始在家教语文,从三字经开始,鉴别文言文,培养读经能力。这种早期的多语言环境和双语教育无疑为他以后的海外汉语学习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虽然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极其复杂,但王的父母并没有放弃回国的希望。一方面,他们攒钱,把一部分收入寄回老家;另一方面,他们观望政局,寻找合适的机会回去。一九三六年,王,五岁,还能记得。就他记忆所及,那一年,全家人短暂地回去探亲,母亲开始一点一点地讲爷爷奶奶的故事。这是爷爷奶奶第一次见到孙子孙女,自然很激动。但尽管如此,老人还是劝儿孙留在南阳工作,继续观望。 这种近乎本能的生存选择看似残酷,但对于当时很多华人留在海外也是无奈之举。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氏家族回归中国的希望开始变得渺茫。不仅如此,战争也开始影响南阳的殖民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英国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1941年底,日军开始入侵英国统治下的马来联邦州,第一批炸弹在怡保爆炸。 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我逐渐发现自己的中国特色太明显,在学校里格格不入。多年以后,王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父母和朋友在家里担心的事情和老师同学在学校担心的事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们的老师讲了大英帝国,讲了帝国在欧洲面临的危机,但是从来没有提到中国,也没有提到【甲午战争】在【南洋】对我们可能造成的影响。就连学校里的中国朋友也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中日】战争。 虽然殖民政府、学校和媒体并不那么关心中国的情况,但王的父母、同龄人和当地的中国商人已经开始为远亲筹集战时资金。他的母亲丁也加入了当地的妇女组织,有时带着王到附近募捐。他的父母也开始带他去新城的电影院看当时在海外华人圈广为流传的各种华语电影,从《八百英雄》、《街头天使》到《木兰从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担忧、迷茫、愤怒等强烈的情绪在父母等成年人中自然转化为救国、爱国、民族兴亡。然而,在当时还不到十岁的王心中,所有的情感都停留在最本真的情感层面,那些情感像层层迷雾,包裹着他只呆了几个星期的中国。 但对于年轻的吴来说,格格不入的感觉可能是他未来不断探索和反思的原动力。作为独生女,他经常会疑惑为什么自己没有像其他中国孩子一样有兄弟姐妹陪伴。母亲甚至告诉他,他们需要足够的积蓄,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回家,所以他们负担不起生更多的孩子。抗战期间除了参加募捐,他的父母很少参加任何当地的庙会、祭祀等社会活动。他怀念怡保的学校和朋友,怀念父母所说的中国和家乡。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和父母更像是旁观者,或者说,是准备离开的住户。 对于准备离开但留在当地的陌生人,还有一个名字。格奥尔格·西美尔(1858-1918)在他著名的小说《1908年的陌生人》中,以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犹太人为例,认为陌生人远近,虽然远近。他们不是流动快的人,而是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在安寨扎营谋生,但与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陌生人有当地人没有的自由,但可能有被怀疑甚至被迫害的危险。他们的位置决定了他们旁观者的心态,但也给了他们独特的机动性和鸟瞰全局的能力。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王在十岁时就对世界地图产生了兴趣。在他十岁生日那天,他的父亲给了他一张彩色的世界地图。下课后,他没有和朋友出去玩,而是呆在房间里,反复搜索大陆、海洋、国家、城市、山脉、河流、岛屿和海峡的名称,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些名称的列表,想象不同名称背后的故事。那张地图让十岁的他意识到,即使是号称永不落山的大英帝国,也只占据了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中国离怡保很远,但在世界地图上并不遥远。 从那一刻起,每当我对自己是谁,身在何处感到不安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地图,想到我的清单,内心就会有一种平静而快乐的感觉。我会想到上海和伦敦,也会想到霍雷肖& middot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和岳飞。但是无论是谁,无论在哪里,那些地方,那些人,都成了地图的一部分。我开始意识到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去了解他们。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那一年的无心之举,让不相容无法忍受。我开始真的觉得,和别人比起来,也许我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二战结束后,王在父母的支持下,于1947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进入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一年后,内战吃紧,一家人最后回国的希望破灭了。王于1957年回到马来亚联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半个多世纪后,先后在马来亚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1986年至1995年任香港大学校长。他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特聘教授。 抛开海外华人学者的各种称谓不谈,也许,一生孜孜不倦探索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家在哪里? 首页不在这里 (作者注:文中引用的片段均由本文作者翻译,出自王自传《家不在此》2018年出版。((华人资讯)海外华人研究开拓者王赓武:身为华人,何处为家?
时间:2020-11-23 13:55:43来源:网络转载点击:
纽约热点新闻
免责声明:以上所转载内容均来自于网络,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只为传播网络信息为目的,非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btr2018@163.com,本人将予以删除。
标题:(华人资讯)海外华人研究开拓者王赓武:身为华人,何处为家?
地址:http://www.namuge.com/xw/20201123/7907.html